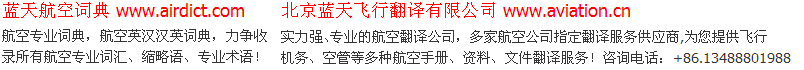云贵高原上哈尼梯田:第一个以民族名义申遗
http://img2.cache.netease.com/cnews/2009/10/9/200910090940415578c.jpg哈尼梯田
http://img1.cache.netease.com/cnews/2009/10/9/200910090940321dd2f.jpg
哈尼族人在耕作
《传奇天下》杂志报道 哀牢山和她坐拥的哈尼梯田正吸引着世界的目光,生活在山上的哈尼族人,默默固守着世代孕育他们的梯田和祖先千年的历史。哈尼梯田现已申报世界文化遗产,一经申办成功,将成为第一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。那么,哈尼梯田究竟有着怎样的奇异之处?没有文字的哈尼族人又过着怎样的生活?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,他们将面临何种考验?
一路温风湿露,经过14个小时的车程,遭遇一场不大不小的降雨后,哀牢山终于横亘在眼前。她宁静温柔、丰盈明丽,又不乏丰腴。哀牢山位于云贵高原,由于地理上的原因,她被来自几千公里外的孟加拉湾的暖流滋养着,当我置身其中时,感觉疲累顿消,身心俱安。
从海拔100多米的山脚,到2900多米的山顶,是总面积约17万亩的哈尼梯田。我从山脚爬到山顶,中间小憩了几次,大概因为年龄已高,我还是有些气喘,观察那些在田里耕种的哈尼人,却个个气定神闲。
终于爬到山顶时,山风坦荡、宏阔,回头俯瞰,一幅壮阔的马赛克豁然展现在我的眼前。而我再仔细寻找那些上山时曾经路过的农人时,竟然遍寻不见。记得我在箐口寨遇到的村民就牵着两头牛在一块呈月牙形、汪满积水的田地里耕地,不过现在我发现整片梯田里竟然有无数的“月牙”,究竟哪一块才属于牛后,已经分辨不清,他和其他人一样,作为小小的个体,已经完全融入毛茸茸的马赛克中。
像梯田一样分布的7个民族
哈尼梯田是哈尼人经过数千年时间方耕耘出的成果。时至今日,多数哈尼人依然过着原始、单纯、周而复始的农耕生活。其实,哈尼族生活的村寨离繁华热闹的县城并不遥远,我在来时曾经感受过县城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,但喧嚣的红尘并没有使这些哈尼人放弃传统,而是一代代固守着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。
哈尼人的祖先最早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边缘,以游牧为生。1000多年前,气候和生存条件的恶劣迫使哈尼人的祖先向南方迁移,最后在哀牢山脉定居下来,由原来的游牧民族演变为一个依靠梯田生存的农耕民族。哈尼人的生活用具也逐渐由鞭具、鞍具变为了谷船、酿酒锅等农耕用品,哈尼族的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—每年他们都有对水的祭祀,鱼成为哈尼族的食物,同时也成为哈尼族的装饰品,甚至在他们的传说中,天、地、人都是鱼的产物,曾经用来驱赶羊群的鞭子被祖先丢在了迁徙的路上,没有留下任何记忆。
哈尼人崇尚和平与自然,他们与7个不同民族生活在哀牢山这片乐土上。令我惊异的是,各个民族竟然循着大山海拔的高低,按照层次划分了居住区域,海拔100米~600多米的河坝区,多为傣族居住区;之上的峡谷区,是壮族居住区;1000米~1400米的下半山区,是彝族居住区;1400米~2000米的上半山,是哈尼族和他们的梯田;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区,是苗族、瑶族居住区;汉族则居住在城镇和公路沿线。
连居住区域竟然也仿佛梯田一样呈立体结构分布,使我不禁对这片土地加深了奇异之感。当我得知这几个民族都坚守着适合自己的生态文化传统时,这种感觉更加浓烈了。
箐口村的村民卢朝贵对祖先的历史比较熟悉,他很肯定地告诉我,哈尼族的祖先从公元6世纪开始南渡恒河进入哀牢山,当时,整个哀牢山区都是茫茫的林海,水源丰富,土质肥沃,于是他们选择了海拔1400米~1800米这段山势作为生存空间。
我们俩蹲在田埂上历数这段历史时,有一人戴着斗笠,骑在牛背上,从梯田对面的土路上经过,温顺的牛偶尔哞哞两声,使绵绵青山显得愈加辽远、苍茫。很快,这幅人牛田园图便消隐在弥漫的云雾中。
从远处收回目光,我问卢朝贵,孕育了诸多民族的哀牢山上有3000多级网格状梯田,它们依山盘绕,层层叠叠,那么,1000多年前很少与外界接触、缺乏现代科学技术和基本水利设施的哈尼人,是如何灌溉梯田的呢?
“我们就是利用哀牢山这个山有多高、水有多高的自然条件。”卢朝贵把手指向山体,并大大地环绕了一圈。
哈尼人知道,只有完整的森林才会孕育足够的水源,以供他们耕种梯田,所以他们从不乱砍滥伐树木。卢朝贵说他父辈就是这样教育他的,他现在也这样教育小孩子。“我们哈尼族上千年都是靠天吃饭的。”卢朝贵笑了起来。
关于这一点,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史军超给我的分析也大体如是,“哈尼族深深知道树和水的关系。没有茂密的森林,就不可能有水源,没有水源,就挖不出梯田,没有梯田,人就没法生存”。
为更好地保护森林,每个村寨中都有护林员。在宝华寨,我曾与老护林员李合法打过交道。李合法每隔一段时间,就要做出一个哈尼山寨专用的警示牌,插到靠近路旁的森林中,提醒人们不要砍伐水源之地的任何树木。我问他,如果人们无视警示牌的存在怎么办?他回答:“警示牌上都说清楚了,谁要是砍了,就要被罚款。”
他向我列举了罚款金额,有罚100元人民币的,有罚60元的,有罚30元的。“条件不一样,看你砍了什么树。”李合法解释道。
据李合法介绍,巡林制度非常严格,一般来说,大的村寨有2个以上的护林员,不论刮风下雨,护林员每天都必须去森林里巡视一圈,这种制度保证了哈尼子孙能世世代代依靠着梯田生存下去。
保护森林与哈尼人的自然崇拜也有一定关系。哈尼人崇拜森林,认为森林是生命之神,他们在建立村寨之初,总要选定一棵高大笔直的树作为寨子的寨神。
(本文来源:网易探索 ) http://img1.cache.netease.com/cnews/img07/end_i.gif
水从“口”出
http://img1.cache.netease.com/cnews/2009/10/9/20091009094021bf896.jpg哈尼族的祖先在漫长的迁徙之路上,积累了丰富的水稻种植技术和经验。从第一台阶设置的水碾,到第二台阶的水碓子,再到第三台阶的水磨,水在哈尼族的历史中发挥了巨大力量。
虽然哈尼人以严格的方式确保了充足的灌溉水源,但从海拔100多米到海拔近3000米,如何灌溉好每一块梯田,对于今天的水利学、工程学、管理学来说,都是一项难题。那么,1000多年前的哈尼人祖先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?
通过哈尼梯田,我了解了灌溉的秘密—自然分水法。这种方法,公平、合理而又科学,避免了因为水的利用而产生的纠纷。哈尼人根据具体情况,还制定了20多条规则,这种关于合理管理水资源的准则,使得每家的梯田都能够及时、适量、均等地得到滋养。
箐口寨村民卢朝贵说要带我见识一下哈尼人的智慧。很快我便看到了一个见证了古老文明的木壳。这是分水的木壳,卢朝贵指着一道壳子和另一道壳子,问我:“你看,为什么在这里有30厘米,那里却只有25厘米左右呢?你看,它们为什么不是等量的呢?”
“为什么?”我茫然地看着他。
“因为我们分水是有方法的。”卢朝贵说,分水多少要根据自己开梯田的面积和挖水沟的投工投劳,还有个人的劳动投入量,即开工时所出力的多少,来决定分水情况。
与箐口寨不同,宝华寨的分水办法是采用“口”的方式。通过对红河州民族研究所所长李期博的采访,我了解到,一“口”就是4指宽,高度是4指的距离,宽度也是4指的距离,如果某户的梯田较多,需要两“口”的话,那么就根据基础宽度酌情扩大。而随便增加或减少水口则被视为“不道德”的行为。比如,大家共同规定的水口,谁也无权擅自改动,否则将处以罚款,罚款是次要的,主要是动了水口的人会背负着道德的阴影。
村寨中有管水员负责分水情况,为确保公平、合理,这个职位必须由秉性正直的人担任。管水员的报酬按照分水比例获取,即每分出去一个“口”,所灌溉的秧田,按收成稻谷的3%给予回报。至于这样的规则究竟已使用了多少年,我问了许多人,都说不清楚。
李期博带我去见寨子里“最严格最有威信”的管水员时,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,为什么叫“口”呢?李期博笑起来,说:“我们哈尼族有个说法,就是一个人4个指头,可以平平地伸进嘴巴,再多则伸不进去,因此,一‘口’就是4个指头。”地处边疆、没有文字的哈尼族,在哀牢山上默默耕耘,崇尚自然、敬畏自
然。这一人类最原始的智慧,让他们创造出了独特的水资源管理系统。
牛后的故事
老一代哈尼人极其重视传统生活,他们对祖先遗留的人文遗产的尊重时常令我心生感动,不过,虽然多数哈尼人仍在固守传统,但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哈尼人却向往现代文明。我在箐口寨接触的村民牛后就一心期望自己的后代能够远离梯田,进入城市生活。
牛后家有4口人,父亲、自己和妻子以及一个3岁大的儿子。因妻子已有近10个月的身孕,牛后和父亲就承担起了喂养牲口等家务。第一次碰见牛后时,他正带着儿子喂牛,当时正值4月底,各家秧田里的秧苗都已长好,马上就要移插到梯田里,哈尼族保持着互相协作的传统,因此不论哪家拔秧或插秧,亲友和邻居都会主动来帮忙,当天,牛后家父子3代牵着牛到亲戚家帮忙,我也一路随着去了。
牛后的父亲拔秧的速度很快,累了的时候,就到田边歇上一会儿,抽上一口云南特有的水烟,逗弄孙子玩耍。牛后趁父亲休息的工夫,又跑去自家的田里,我问他做什么,他说拔些蔬菜,晚上给妻子熬汤。
牛后还有一个弟弟,在昆明工作,弟弟和弟媳没有生育能力,一直想把牛后即将出生的孩子过继过去。他弟弟认为,让孩子从小就接受现代化的教育很重要。牛后自然愿意过继,但父亲不同意,老人担心孩子进城后,哈尼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会在后代身上断送。他悄悄对我说,他刚才插秧时已经打定了主意,准备在哈尼人每年一度的节日上跟牛后彻底谈一次。
为什么要选在节日谈话,老人也有考虑。在他的设想里,哈尼人节日里特有的文化气息,也许会留住儿子向往城市的脚步。
哈尼族有许多节日,2月份祭寨神,3月份开秧门,6月份是苦扎扎节,7月份是撵鬼节(把寨子中的瘟神撵出去),8月份是祭梯田神的节日(与农业稻作文化有关),这个月份还有一个家庭的祭祀,叫吃新米饭节,9月份是祭仓神,10月份后就是十月年。其中最重要的节日是昂玛突节,昂玛就是寨神的意思,这个节日是祭寨神、与寨神同乐的日子,祈求村寨在寨神的保佑下获得发展。
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史军超告诉我,节日开始时,硭鼓手会在村中打锣,催各家各户生火做饭,每户要准备12道以上的菜品。之后,他们要端着饭菜来到寨子正街,那里已设好龙头,头领也已端坐在头一张桌子上。头领在节日里是神的代言人,饭菜摆放好之后,先由家庭主妇排队依次向他的桌子上献菜,由他的副手一个接一个象征性地收一些,然后,再从他的桌子上给女人拿回来一点,意味着向寨神敬献。最后,头领示意,长街宴可以开始了,大家便欢声笑语地边吃边叙家常。
在节日上,人们总要邀请洞蒲寨古歌传唱者(贝玛)朱小和来到现场为大家唱歌。在牛后老父亲的眼里,这种古歌简直就是难得的爱祖先、爱哈尼的思想教育课。
哈尼族的古歌,实际上是整个哈尼族文化的一个载体,史军超向我讲述它时,把它形容成一条船,这条船把哈尼族所有的东西装到里面去,然后在历史的长河中一路向我们走来。而朱小和这样的贝玛则被认为是哈尼人的知识分子,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。哈尼民族没有文字,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就是依靠各个村寨的贝玛通过父子或者师徒传承,一代代说唱延续下来的。
为什么要一代代说唱,史军超在介绍古歌的缘起时,说到一个传说,以前掌管书籍的被称为摩批,即祭师,他是文化的传承人,一次在过河时,河水越来越深,他走在河中只好用嘴巴叼着书,结果一个波浪扑过来,他不小心把书吃到肚子中去,因而整个民族的文字,也就保存在摩批的肚子中。为了不成为历史的罪人,他开始唱歌,通过说唱,把历史面貌展现出来。
古歌传唱的内容和形式有很多,其中3大部分较为清晰,即哈尼人的起源、哈尼族的迁徙,以及定居哀牢山。对于生活在梯田上的哈尼人来说,这些古歌是他们了解祖先最主要的途径。
但迁徙史诗一般是不唱的。除非有老人死亡,说唱者才唱迁徙史诗,他从寨子里,走一程唱一程,引导亡者的灵魂返回诺马阿美(四川雅砻江、安宁河一带)的祖先所在地。
牛后的父亲有一首最喜欢的古歌,里面传唱的是哈尼人的祖先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搬迁,从中国西北青藏高原边缘的虎尼虎那,一直搬到西南的哀牢山的过程。“走吧兄弟姐妹,这里不再有我们的家园;走吧兄弟姐妹,舍不得也要舍得了,要走多少步,才有我们的家园。”从这首歌里,老人总能切身地体会到祖先寻找家园的艰辛和磨难。
在箐口村哈尼族博物馆中,还保存着古代哈尼人过河时使用的独木舟、作战时使用的弓弩。这些文物仿佛会说话,它们告诉每一个注视者,哈尼人的历史,就是流浪和迁徙的历史。但幸运的是,哈尼人最终找到了乐土,“瞧那寨子脚边开出层层梯田,层层稻秧比罗比草兴旺,哈尼寨子布满哀牢山”。
这些让人沉痛又让人振奋的歌曲,是牛后的父亲最看重的东西。他想通过传统的节日活动,让牛后在聆听祖先历史的时候,慎重思考后代的未来,增强他对土地、水和梯田的深刻感情。他在插秧结束后曾告诉我,他不过就是想让牛后明白一件事,哈尼人不应该离开梯田。对于父亲坚守梯田的心情,牛后心里很清楚,但清楚是否就意味着认同呢?
牛后的父亲满怀期盼地等待着节日的到来,不过,节日还没莅临,牛后的娃娃突然提早降临了。
呱呱坠地的孙子,使牛后的父亲顾不上盘算节日谈话的内容了,他计划着什么时候带孙子到梯田里举行哈尼人传统的出生仪式。每个哈尼人从出生到死亡,都跟梯田有着看不见的联系。一个哈尼族婴儿出生13天后,需要举行一个新生婴儿的出门礼,具体仪式是:哈尼人身着盛装,在梯田里跳起舞蹈,一边为增添新生命而庆祝,一边祈祷村寨香火更加旺盛。然后,新生的婴儿就要被母亲背出家门,来到梯田里。有时还要邀请寨子里的小男孩,携带小锄头,象征性地在梯田里挖一下。
儿子的诞生也让牛后十分欣喜,他在市场里为妻儿采购时,再次认真地思考了儿子的未来,并决定在晚饭后与父亲好好谈一次。他有些问题要问问父亲,恪守哈尼人的传统固然重要,但拒绝文明和科技就是最好的选择吗?把儿子留在哈尼梯田,还是送入一个崭新的环境,对孩子、对民族、对国家的将来又会有怎样的不同?难道儿子与父亲与爷爷,都应该拥有一模一样的未来吗?
坐在返程的车上,我不禁陷入沉思,牛后的父亲还未来得及找儿子谈话,面对儿子的发问,他会作何感想?
车窗外掠过成片的梯田,因暮色渐沉而呈现出黑幽幽的颜色。我想,无论牛后新添的儿子去留如何,哀牢山的哈尼梯田都是亘古不变的,日出日落,春华秋实,生生世世。
本文来源/《传奇天下》
(本文来源:网易探索 ) http://img1.cache.netease.com/cnews/img07/end_i.gif
页:
[1]